按照常例,今日清明。 依往年,这也该是个阴雨淅朦,天公黯然的日子。人们或循着拥挤的人流前往郊区墓园,或开着自家汽车行驶在新铺就的回乡公路上。约莫半年前,我坐在车后座抱着骨灰盒,为祖辈入土、归根。那天,车稳当无声地开到了村口旁的一座矮山下。停毕,除了我,大家下车,等鞭炮排好、响起,车门开,人循着鞭炮的音迹上山。骨灰盒落下,请来的工人们开始挥铲,刻碑的抓紧做最后的完善。 入土的那天,天气晴朗,我的心情却是黯淡的。诚实地讲,更多的不是为了先人,而是自己。不巧那段时间在工作中受挫,整日整日的心灰意冷,睡很久的觉不愿起床,发很久的呆也不想做任何事。回到家乡的祭奠像是一次被迫的分隔符,“生活还要继续”、“一切都会好起来”的直觉在心灵深处鸣响却也无济于事。 今天想起来,再写下来的时候,快半年过去了。生活确实还在继续,一切也都变好了。“时间”几乎是一种不存在的慰藉。如果你还愿意的话,我也愿意在清明的时候给你讲一个时间的故事。
二零零六年我从苏州毕业,回南京上班,一时也挤在大姐家。十一月时要出差深圳一个月,临走前几天,三姐夫忽然发起低烧来。大姐在家给他挂水,好了没一两天,就又发起低烧来。店门因此关了几天。我到深圳的第十天,给家里打电话,妈妈才跟我说,三姐夫前两天在家里忽然摔倒,不省人事,送到医院去了,好容易才醒过来,差点没命哩!我大吃一惊,问是怎么回事,妈妈也说不清。总之大概是发烧太久,病毒侵到什么要紧地方去了。她让我不必担心,我也便不甚在意,以为很快会好起来。
一个月后我回南京,赫然看见小房间的玻璃门上几道裂痕,妈妈说,那是你三姐夫摔倒时撞的。我这才知道原来他还在医院,情况很严重了,陆续查出了许多先前不曾有的毛病,肺、心脏都有了问题。他们的存款已差不多耗尽,姐夫的病因却还找不出,几次请鼓楼医院和其他医院的医生会诊,都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。到了晚上,大姐回来了,让我帮她打字,写邮件给一位治疗心脏有名的专家,求教病因。她坐在我身边,非常仔细地描述三姐夫的临床症状,遇到不会打的术语,我就问她。房间吊顶上白色的日光灯冷冷昏昏,此外我们都不大说话。第二天,那边回了邮件,终于提出了可靠的病因。接着决定做心脏手术,要八万块,大姐二姐把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,又去别处借了一些。手术完后,医生说,非常成功。大家都松了一口气,终于要没事了啊。 这两个月里,妈妈每天下班回家做饭,再送到医院去。有时是大姐和大姐夫送,我回来后,有时是我和那时的男友送。是最冷的冬天了,人的手冻得生疼,走在街上,呼出的气长长的一片白。他骑电瓶车带我,一点一点穿过冬天傍晚白雾与尾气弥漫的城市,到了医院,只有保温瓶里的饭菜还滚热。病房里暖气极足,三姐坐在床边,伏在被子上,见我们来了,就起身拿碗去开水房烫干净,一勺一勺喂姐夫吃汤和一点其他流食。自生病后,姐夫已瘦了很多,性情也变得脆弱,在心脏手术前,几乎不能说话,见到我们,轻易就会流泪,见到园园时,更常呜呜哭出来。园园还太小了,有时候她抱着爸爸一会儿,有时候就在一边玩。因为姐夫的病似乎有传染的可能,我们并不常常把她带到医院来。 我去医院看姐夫时,看见床头那些吓人的仪器,尤其是心电图的仪器时,就觉得很怕。因为在电视里,这仪器常是预示着不好的事情。有一段时间姐夫要靠氧气瓶才能好好呼吸,只有吃饭时才拿下。三姐有时去洗碗,要我看着那些仪器,我看着显示屏上的数字变化,极为紧张害怕,因为那数字有时会变到三姐说的“危险数值”上去。我想叫不敢叫,好容易等到三姐来了,赶紧指给她看。她大约已见得多了,心脏锻炼得强健一些,轻轻跟我说:“不要紧,过一下子就会好的。” 手术后十来天,就是过年。征询了医生的意见,说,可以暂时出院了。大家以为大病终于初愈,值得回家好好庆贺,因此三姐和三姐夫包了车,和他的姐姐一同回句容过年。打电话给三姐,她说还好,我们也就放下心来。到了正月初四的下午,却忽然觉得气闷,夜里大约是咳出血来,三姐连夜包了车从句容回到医院,医生检查后,却说,没有什么问题,好好休息就是。初五中午,是爸爸去给姐夫送饭。吃过饭,姐夫跟三姐说:“三子,我想睡一会儿。”三姐便让他睡。傍晚时醒来,抱了下三姐,笑着说,哎哟,终于是醒了,我睡的时候很怕就这样一睡醒不来了。三姐笑他傻。然而就在晚上八点多,他跟三姐说,三子,我想打个嗝。话才落,人已昏了过去,休克了。抢救终是无效,只二十多分钟,就没有了希望。那时候医院里,只有爸爸和三姐两个人在身旁。 那天我和妹妹都在南京的郊县,晚上我忽然接到三姐电话,在拼命地哭,喊:“你快点回来,你姐夫快不行了!”而我已没有回去的车了。过了不到半小时,便接到大姐电话,说三姐夫已经不在了,想办法马上回来。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到医院,连人也不得见了。三姐和园园随车回乡下发丧,而我们站在医院门口,一家人冷冷的相向无言。那一天园园是和二姐一起在江宁,二姐接到三姐电话,拉了园园发足狂奔,四处打车打不到,最后是一个开私家车的人送了她们过来。姐姐说,园园到了医院,拼命地抱了爸爸的脖子哭。她还不很懂得“死”的意思,那时候却也知道悲伤和害怕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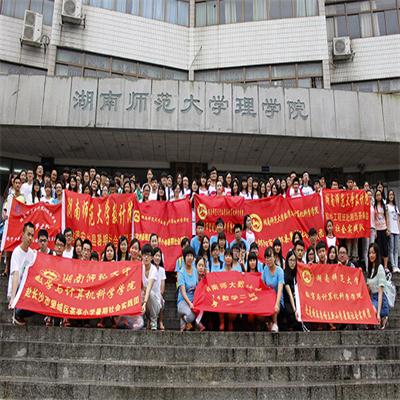

网友评论 已有 0 条评论,查看更多评论»